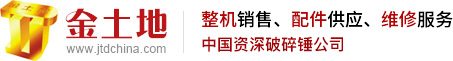牺牲住房公平 中国城市开发掀起新一轮“折腾”浪潮

图:广州城中村
开发城市浪打浪,前浪倒在沙滩上。尽管4万亿刺激计划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有2800亿,棚户区改造已成为许多地方的政绩新样板,但如果以往在城市开发中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总结与扭转,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就将复制出一处处新的尴尬,也将有新人在反腐中倒下。即便短期做到了保八、保十,实际又有多少意义?城市,既不是地球的伤口,也不应在人群中制造分裂。
胡锦涛总书记说,“不折腾”。
当“石家庄速度”遭遇金融危机 (特约记者 黎光寿 发自石家庄)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花园村,这个曾经因为拆迁争议而几乎陷入“停摆”的城中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施工场地,新的楼房正在建设之中。
但2008年事情起了变化。“3月28日,花园村开始发放一本关于旧村改造的宣传手册,大约也只发放了50多户,29日突然贴出通知,要求村民29日下午到村委会去拿房号。拿房号的村民发现,拿到房号以后就得同意交房,还签订了一个协议,4月5日就要拆迁。”
“4月5日走了一批,拆迁公司进村以后,一些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堵塞了村里的好几个路口,还有一些‘小平头’经常在村里的各个路口晃悠,村里水、电和电话逐渐不正常,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陆陆续续又走了一批。”李淑英说。
与花园村类似,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2008年被拆掉的城中村共有22个——他们均属于该市政府2002年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的二环内45个村庄之一,但因村民、村委会和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不一致,2007年五年计划结束时,多数村庄的改造还停留在博弈阶段。
对执政者来说,改造城中村一直以来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老大难”在2008年开始得以解决呢?因为石家庄从2007年底以来开始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行动,“从2008年起用3年时间在全省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简称“三年大变样”。
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对记者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三年大变样”,实际上就是“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城市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城市魅力初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等五个方面。从微观来看,“三年大变样”则包含了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城市特色塑造、景观环境整治等20个方面的内容。
焦庆会对记者说:“2008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和景观环境整治,主要的特点就是拆,以拆为主;2009年是边拆边建,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面貌的改变。”
改造京津烂围墙
2007年12月10日,河北省政府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概念。半个月后的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吴显国做了“做好‘三篇大文章’、实现‘三年大变样’ ”的主题报告,“三年大变样”正式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众所周知,石家庄的历史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石家庄村交汇开始。1947年,石家庄建成区仅12平方公里,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这所城市奇迹般地崛起。2008年,石家庄已形成了6区5市12县的规模,主城区人口达215万,列全国特大城市第28位。
“但石家庄一直是一座缺少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土生土长的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梁勇认为,石家庄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已成为河北省省会,但几十个城中村的原著民和外来移民,使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典型的文化上耗散的城市,一座多元移民为主流群体的城市。
而因为文化认同感的缺乏,石家庄至今有句民谣“张书记挖,李书记填,王书记来了不给钱”,基本体现了近年来石家庄的现状。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告诉记者,由于河北环绕京津,河北省的多任省委书记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和发展似乎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环京津贫困带”在坊间被戏称“河北是京津的烂围墙”。
2007年8月,张云川从国防科工委主任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开始了他在河北的“新政”。张云川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干出成绩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设,“地方政府事情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主观上一定要有个抓手”。张云川认为:“河北省作为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省份,应当有更加开放的眼界、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举措。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势,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谋划发展、推进发展。”2007年10月29日,张云川在河北省委七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希望城市建设“力争每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2月24日,在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张云川说,不要担心拆迁改造对GDP会产生多大影响,有社会资本积累必然会重组产业,有土地储备必然会引来新项目:“我们搞城市改造不是拆多拆少的问题,而是该拆的是不是都拆了。一个城市要搞一轮改造,3年左右的时间拆不到建筑面积的10%,就谈不上动真格的改造。”
3天后,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省会城市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张要求石家庄要作出表率:“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不成现代化城市”,“明年(2008年)是实现省会三年大变样目标的第一年,这一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有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拆迁改造,还是新建项目,都要有大的动作,确保有一个好的开局”。
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后不久,石家庄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政府各部门和所属各区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三年大变样”指挥部,并由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挂帅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下设综合处、拆违处、综合整治处、稳定保障处、旧村改造处、督导巡查处等6个处室,从2008年初开始运转,4月份起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拆迁。最初“三年大变样”政策出台的时候,一些地市还处于观望状态,当全省各地市的官员到石家庄考察以后,他们一下子被连续几公里的壮观场面镇住了,回去以后各地市的动作一下子就起来了。
京津烂围墙石家庄速度:一次现代化的跃进
在石家庄市规划局的网站上,有多幅关于“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图。许多处于被改造中的城中村,已经被描绘了非常气派的大楼和住宅小区。该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藤斌认为,正在进行的“三年大变样”工作只是过去长期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我心目中的石家庄应当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藤斌说,石家庄市从建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次规划,焦庆会告诉记者,一定要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城中村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冲突。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避谈“三年大变样”的话题,不过藤斌所说的在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的调整,在他看来是必由之路,也是他向石家庄市委提出并被采纳的建议。在他看来,即便没有“三年大变样”,石家庄市也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也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也要将一部分城市功能外迁,只是“三年大变样”把这样的目标提前和具体化了。
而河北省《文史精萃》杂志总编辑石玉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理解张云川书记和河北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但由衷地讲,“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过去我们超越客观条件,做了许多主观上想利国利民的事情,结果教训很深刻,造成的恶果非常惨痛。”
“‘三年大变样’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但我们是否具备了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能不能落到实处?是否超越了河北省的发展阶段?”
“拆迁需要1000多亿,建设约需要8000亿,财政有钱吗?现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后能建起来吗?让下边去找钱,能顺利找到吗?”石玉新说:“三年大变样要求思想大变样、观念大变样,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限定时间的大拆迁。”
危机里的温度
“三年大变样”的最初设想是,通过城中村的拆迁和部分城市功能的外迁,在城内腾退出一部分土地,吸引战略投资者,重新规划,一次性建设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总投资大约为1400亿元。2008年上半年,石家庄引进了香港嘉里、大连万达、青岛海尔、北京金隅、中城建等战略投资者,参与开发建设。
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影响到了石家庄
房价的下跌也影响“三年大变样”的进行。一位热心关注者告诉记者,从石家庄本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08年9月份以后,石家庄对城中村的拆迁逐渐冷却下来,剩下的就只是拆除违章建筑,禁止破墙开店,“但声音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的讲话似乎也在印证着全球金融危机中石家庄的“温度”,他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也透露, “石家庄市年计划土地出让收益38亿元,目前仅完成9亿元,不到年度的1/4。”
在胡春华的讲话背后,就是参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战略投资者撤出的小道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轮不到国有建筑公司,因为他们一般追求质量,机制不灵活,不能给回扣,该村找到该国有建筑公司,说明私营的建筑公司或者开发商都已经不愿意上前了。”石玉新说:“关于垫资和给工钱的问题,一般的原则是要么建筑公司先垫资,盖楼的时候按时给工钱,要么不垫资先盖楼,盖到一定层数再给钱,二者只能选其一。该村的开发方式,等于空手套白狼。”
谈固村一直是石家庄城中村的骄傲,有3000多户,一直以来就有“金谈固”的说法。在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谈固村也是重点,可因为较为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改造。在本次“三年大变样”工作中,谈固村临近石家庄市主干道中山东路的部分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拆迁,河北省将谈固村拆迁树为典型,各地级市领导前往考察,从而推动了整个河北省的拆迁工作。
记者到该村采访的时候,就有村民说,原先和该村签订协议的开发商跑了,后来的开发商和村里讨价还价,一般联合开发的分成是村里和开发商五五分成,原先的开发商跑了之后,村里能够接受的底线谈判价格是建房之后四六分成,可新的开发商却坚持村里只能要35%,开发商要65%,谈判不欢而散。
当记者询问石家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运江,是否需要国家或者社会给予相应支持时,谭说:“‘三年大变样’是一项地方的决策和政策,我们是当事人,只有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银行助推“石家庄速度”
2008年12月28日,主管城乡规划等方面工作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洪江去职。这是“三鹿事件”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去职后石家庄市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当地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也未见其他媒体有深入报道。
不过“三年大变样”没有受到这场人事变动的影响。石家庄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3.93 -0.25%][3.94 1.55%]等大银行的支持,土地交易回暖,引入了大连万达等战略投资者。拆迁改造在2008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石家庄速度”。
2009年1月,石家庄市提出了2009年到2010年“三年大变样”的五大目标,推出了总投资1111亿元的五大类146个项目,其中有省行政中心广场等20大献礼工程需要在建国60周年前夕完成。2月10日召开的石家庄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车俊提出要创造“石家庄速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拆迁改造是城市建设的第一难,也是城市建设的第一关,石家庄更是如此。根据石家庄市的规划,2009年要完成“三年大变样”工作量的70%,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艾文礼要求所有的行政干部“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经验”,迅速推进“三年大变样”工作。
城市拆迁领先全国的“一天一栋楼,4个月修两条路”的“石家庄速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府创造。
桥西区辖区内裕华路、槐安路改造只有4个月的工期;民心广场工程要10月1日完工——这三大工程占石家庄2009年拆迁总量的1/3。2月15日,石家庄市召开“两路”拆迁动员大会,要求桥西区2月底前必须拆除裕华路沿线的95家单位和居民。当天,桥西区就成立了拆迁指挥部,区领导每三人成立一个分包组,同时还成立了7个突击组,由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负责,专门负责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的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裕华路和中华大街交口的工行中华大街支行大楼,总建筑面积6400多平方米,担负着周边省直、市直和居民的金融服务业务,不仅业务量大,并且地下还有金库。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当天下午5时接到拆迁任务后,立即召集拆迁队伍,制定拆迁实施方案和突发事件预案,签订拆迁协议。当夜,他们动用了9台勾机连夜进行了拆迁。第二天凌晨5时,整个大楼被拆平。
此后,沿裕华路4栋超过6000平方米的建筑,两天全部拆除;中裕立交桥周边7个产权单位、286户居民的3万平方米建筑,11天全部完成动员和拆迁;槐安路9.7公里高架桥、裕华路14.5公里路桥改造工程,4个月内必须完工,而正常则需要一年半,开工一个月完成的工程量就超过30%;全长3.6公里的和平路高架桥工程,原计划18个月完工,现在提前到8个月完工……
繁华都市里的第三世界
广州有138个城中村,在政府眼里,它们都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痼疾。
拥有700多年历史的石牌村离猎德村不远,同样位于天河核心区域。这条老村子周边的土地早早就被政府和开发商征完了,旁边建起了高楼大厦,商铺林立,已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然而,城市高楼虽包围了石牌村,但这个村子里的原生态村民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只是窝缩在高楼之间,形成了阴暗角落的一个特殊生态群。
从繁华的石牌东路一条小巷拐进村子,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握手楼”,而是更亲密接触的“贴面楼”、“接吻楼”,低矮的楼房对户阳台紧紧贴在一起,遮天蔽日,以致在初夏阳光普照的下午,楼与楼的夹缝之间居然透不进一缕明亮的光线,所有人和物都被笼罩在沉沉的阴暗当中。
就是这片狭窄阴暗的区域里,一共有3656栋房子,据村民称,村里最神奇的一块宅基地明明不足10平方米,上面却能盖起4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些违章建筑和脏乱景观,与天河繁华的城市面貌显然格格不入,更遑论里面层出不穷的治安问题总是让政府伤透脑筋。
早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
然而,虽然9年前就定下改造的主旋律,但直至现在,称得上改造完成的只有一两个小规模的自然村,除了猎德村,真正大规模的成功改造经验至今没有出现。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一些城中村的负责人表示,几年前就依照政府要求递交了本村的改造方案,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获批。像石牌村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声称要改造的村子,至今竟然还没有定下正式的改造规划。
慢慢慢,还是慢
显然,与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的豪迈风格相比,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曾向媒体坦言,目前城中村改造进展“十分慢,慢得让人心寒”。
让官员心寒的背后,是城中村生态里复杂的利益体系。
“石牌电脑城之所以这么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牌村。”一位在电脑城卖配件的店主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1993年,石牌村集体企业三骏集团与发展商签定协议,在石牌西投资兴建室内电脑城,随后,天河电脑城、金硅谷等一批电脑市场才真正在石牌西成行成市。而石牌村的大量廉价出租屋不但为这个华南最大的IT商圈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提供了廉价货仓。
在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城中村改造涉及原来的经济方式转型,牵一发而动全局。作为城中村的主体,村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出租经济能不能持续?改造后租金水平提高,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如何安置?
从改造用地,到资金投入、拆迁补偿、政策扶持……整个利益关系一旦无法重新理顺,改造进程缓慢就是必然的。